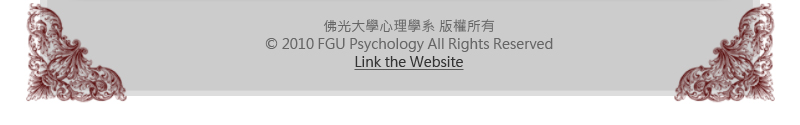誰說我是反科學?—科學旗幟下的另類活動 / 李國偉
當代雖然是一個科學高度發達的時代,但是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即使在科技強權的美國,科學教育卻有重大的不足。1991年美國的總統科學顧問在一份提交國會的報告裡說,美國公眾的科學素養之低,低到有半數被詢問的人,不知道地球繞太陽一周需要一年時間。同期間另外一份報告指出,以最寬鬆的標準來衡量,美國成年人裡至多只有7%算是有科學素養,13%對科學的過程有最低限度的認識。40%不同意「占星術一點也不科學」這種說法。相映於這種民眾科學教育背景,各種「反科學」的活動興盛,似乎也就不那麼出人意表了。在台灣好像沒有做過科學素養的調查,不知道跟美國的狀況有多大的差別。但是社會上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實在讓人不敢有太樂觀的期望。
在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裡,不管人民的科學素養多麼貧乏,他們仍然有權力參與涉及科技問題的決策過程,因而不免會加大產生錯誤決策的風險。哈佛大學物理與科學史講座教授G. Holton在他的《科學與反科學》[1] 一書中說:「歷史一再顯示,對科學及其世界觀的不滿,終會轉變成憤怒,以致於跟更陰狠的運動掛起勾。」雖然他說「『反科學』這個名詞概括了太多彼此差別很大的東西,它們所共同的部分,只是都會惹惱或威脅到那些自以為比較開明的人。」但是他認為比較精緻的反科學者所拿出來的「是一種精裝的、有機能的、有潛在威力的另類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包容了一種與通常科學迥異的『科學』。這種世界觀的歷史功能就是要在最廣泛的意義下,讓(一般的)科學喪失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的正當性。也使得傳統上科學要主導人類進步的意義與方向,這一類擴張性的雄心企圖喪失正當性。」
從思想的淵源上來看,為現代科學尋求理性基礎的努力,在邏輯實證主義及其相近學說中達到一個高峰。之後就產生以Kuhn與Feyerabend為代表人物的反擊,使得在科學典範的轉移中,理性的作用大大降低,而科學追求最終真理的企圖,被當作空幻的妄想。科學賴以獲得穩定知識的方法基礎,也被貶抑到與其他反科學傳統等量齊觀的地位。另外一條動搖科學正當性的思想進路,來自歐陸的哲學傳統,Heidegger抨擊科學與技術使人變得非人化。而他的追隨者,特別是法國走後現代路線的人,把科學理解成一套敘事系統,通過科學語言的解構,什麼叫真實的客觀標準不復存在。而在權力、官僚、國家的支配下,科學也幾乎處處喪失了聖女的形象。
從社會活動的層面來看,衝擊科學的行動,常常涉及價值的取捨,也就是從倫理的角度,鬆動傳統上科學家未及深思或反省的選擇。像是反對核能發電,恐懼化學添加劑對環境的破壞,擔心生物遺傳工程產生難以逆料的後果等等,都對科學發展發生煞車作用。在醫藥方面,雖然西方正統醫療技術突飛猛進,人類的壽命明顯延長,可是各種另類療法也相對的愈發昌盛。另外在爭取解釋世界的權威上,Darwin的進化論不斷遭受愈來愈精緻的創造論反撲。這種現象特別在美國最為嚴重,近期所謂「智慧設計說」更是用科學的語言,完成高度細緻的包裝。
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與天文學並駕齊驅的是向占星術的回歸,與心理學、認知科學相伴隨的是特異功能的彰顯,與太空旅行同步的是傳言UFO與外星人到訪,在在都是超自然世界觀與自然世界觀的抗衡。對一般常民而言,這些另類現象提供的解釋,能與他從傳統接收來的說故事式的相互關連性接合,遠比正統科學提供的因果關係解釋更容易下嚥。人喜歡從接觸異乎尋常的事件裡得到刺激,又從樸素的超自然世界觀中得到某種秩序的安頓,因此對一些反科學現象的迷戀,似乎有難以避免的趨勢。或者反過來說,要建立穩固的科學世界觀是一件需要著意努力,往往非常不容易做好的事。
科學家自己從事科學研究,能掌握科學運作的方法,好像不應該跨越科學能建立的因果鍊範圍,去跟常民一樣向超自然尋求解釋。特別在心靈與物質世界的互動方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應該能有理性存疑的自持力。但是事實不然,中外都有一些很優秀的科學家,在對某些宣稱異乎尋常現象的研究手段上,都跨越了科學社群通常能接受的範圍。
我們並不是說存有一定的禁區,科學研究絕對不能碰。也不是說那些另類的手段,就絕無可能產生有意思的結果。遠一點來看,像Newton在宗教與煉金術上的一些偏愛,對他提出萬有引力的思想,是產生過某種程度的提示作用。然而科學在當代已經到了如此高度發達與成熟的程度,科學社群也無形中發展出一些大家不言而諭,基本上不會冒犯的規範。這時候如果還要從事那些越界的活動,就不免遭遇到科學社群的質疑了。
科學家另類活動的著名例子中,首先值得提的是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他與達爾文同時創立以天擇為基礎的演化論,是一位愛好廣泛、博學多才的動植物學家。他從1862年開始閱讀一些靈學方面的著作,起初也認為都是一些欺詐、騙術和愚昧的行為。但是後來結識一位倫敦有名的靈媒Marshall夫人,經過三年的研究,變得完全相信那些現象是由神靈產生。他曾經告訴友人:「在過去兩年裡,我親自目睹了各種超常現象,它們能在不同的條件下出現,以致於只要有疑點產生,就會有其他現象對此做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見得越多,認為欺騙和幻覺的說法越站不住腳。我認為這些是真實的自然現象,就像我認識的自然中別的奇怪現象一樣確切。」到1875年Wallace出版了《論奇蹟與現代唯靈論》一書,替那些裝神弄鬼的現象背書,甚至要人相信歷史上傳說的神靈故事。
雖然Wallace與Darwin一樣主張生物的演化論,可是到了涉及人類智慧的問題上,Wallace就脫離了自然的、因果的解釋,而去神靈世界尋求超自然的緣由。1903年他出版《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一書,列舉許多證據,說明動植物演化都是由超自然的智能所設計的,它們的演化全是為了人類的存在而作準備。
Wallace本人應該是一位誠實的君子,因此他不相信靈媒會有舞弊詐欺的行為。他甚至以證人的身份出庭,為一些被揭穿是騙子的人物辯護。Wallace的這種態度是有代表性的,科學家自己謹守科學研究的基本規範之一,就是必須誠實面對自然,於是推己及人認為參與研究活動的人都會遵守這種不作偽的規範。有人把這種作法比擬為法律上的「無罪推定論」。可是時至今日,從非常多的歷史實例看來,涉及各種所謂超能力的檢驗裡,被檢驗人嘗試作弊的可能性極高。為了使實驗的可靠度經得起考驗,防偽的措施必須嚴密做好,這與「有罪」、「無罪」不相干,也不必然在懷疑實驗者的誠實與否。而應該很平和的當作一項實驗設定的規範,任何防偽措施不周延,以及沒有防偽專門人員檢驗的實驗,就不該當作有效的實驗。
科學家作實驗的對象如果是自然的物件,絕對不必擔心自然會造假,擔心的只是實驗設計得精巧不精巧,實驗執行得細緻不細緻,所得的結果能不能判定預設的假設是否為真。但是優秀的實驗科學家,不見得會懂得如何作偽、如何防偽。因此在實驗中邀請防偽專家參與有其必要,有時也許一位有經驗的魔術師便足夠滿足需要。
1972年及1973年以色列有名的特異功能人Uri Geller走訪史丹佛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現稱SRI International,與史丹佛大學無關),接受Harold E. Puthoff與Russell Targ兩位物理學家的檢驗。1974年10月18日英國著名的科學學報Nature還發表了他們的論文。他們報導了一項實驗,把一粒3/4英吋立方的骰子,放進一個3×4×5英吋的鋼盒裡,由實驗者搖晃鋼盒後再放回桌面,由Geller寫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數碼。兩位科學家沒有具體說明他們是否採取有效的防偽措施,只是說他們保證受測人決無法作弊。結果在10次測驗裡,Geller兩次放棄給出答案,而其餘8次完全猜中。不過在Nature刊印論文之前,英國有人發表調查報告,指稱Geller每當有魔術師在場時就會失敗。後來因為著名魔術師Randi大舉揭露Geller的作偽,使得他的表演很少再有人相信了。但是Geller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他不斷的跟揭露他的人打誹謗官司,堅持自己真正有超能力。
心靈活動是否能影響物理世界,自古就是令人非常好奇的現象。雖然人文學者與宗教家對這類問題,早有非常多的見解,但是一日沒有得到科學的充分證據,都只能算是見仁見智的意見罷了。而當科學理論與實驗方法都大有進步的時候,還要所有科學家裹足不前,不敢進軍探勘科學邊緣的特異現象,也是不可能的狀況。這類研究並不該有什麼先天的「原罪」,有些科學家願意冒著一無所得的風險,但又胸懷一旦有得即可顛覆傳統的憧憬,像地理上的探險家一樣,非要親身走一趟不可,其實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
1882年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一些院士,成立了「心靈研究學會」。會員包括有Rayleigh爵爺,J. J. Thomson,Oliver Lodge這些著名的物理學家,學會的宗旨是要研究「在一般公認的假設下無法解釋的人體功能,不論它是真的還是想像的。」1882年之前英美的特異功能可說是「唯靈論」時期,自從「心靈研究學會」的成立,就進入「心靈研究」時期,直到1935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學家J. B. Rhine成立「超心理實驗室」,才確立比較有系統、有控制、使用統計工具的研究階段,自此之後可以說是進入「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時期。Rhine研究的現象分為兩類:一類叫超感官知覺(extra sensory perception,縮寫為ESP),包括傳心術(telepathy)、天眼通(clairvoyance)、未卜先知(precognition);另一類叫念力(psychokinesis,縮寫為PK)。
超心理學經過七十年的發展,成立有國家的或國際的學會,出版了國際性的學報,也在一些有聲望的大學裡建立研究室。從形式的條件來看,它與一般正統的科學學門差異不大,並且獲得的經費補助也不容忽略。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位Puthoff,要在1979年美國科學促進會上發表ESP論文而被接受時,著名物理學家John Archibald Wheeler公開反對,他說:「每一門成其為科學的學科都有數以百計的夠硬的結果,但『超心理學』卻拿不出一個。為了科學的榮譽,要求『超心理學』拿出一個、兩個或者三個經得起挑剔的結果,做為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的條件,這有什麼不公平嗎?」可見形式上的符合,並沒有贏得科學家的普遍認同。
但是對超能力的興趣,並不侷限在科學家想判定存在與否的範圍。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運用天眼通來觀察敵方設施就非常感興趣,前後有二十多年之久,CIA補助前面提過的史丹福研究所,以及後來的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簡稱SAIC),從事ESP與PK的研究。1995年CIA委請美利堅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評鑑這些研究結果,一方面判斷到底有沒有超能力作用,另方面評估這些作用是否有益於情報工作。評鑑工作主要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統計學家Jessica Utts與奧瑞岡大學心理學家Ray Hyman執行,但是兩個人對實驗數據所顯示的統計意義,有截然不同的判讀。Utts相信確實有高於純粹隨機猜測的正確比例,因此超感知的現象真實存在。而Hyman認為Utts的分析有方法上的缺失,因此不應該得出肯定超感認知的結論。事實上於1991年,Utts在統計學裡有聲譽的Statistical Science學報上,就發表過一篇檢討超心理學使用統計方法的論文,但是在其後的多位專家評論中,並沒有得到大家一致的支持。統計界的大家Persi Diaconis甚至直指該篇研究有關鍵性的差錯。
但是在支持Utts論點的科學家中,也不乏聲名卓著的人物。最令人注意的是劍橋大學Cavendish實驗室的Brian D. Josephson,他曾經因為發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量子效應,而於1973年獲得物理學的諾貝爾獎,並且是當時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Josephson因為多年迷戀研究這些心靈現象,卓著的聲名已經不見得都是令名了。2001年英國皇家郵政為了慶祝諾貝爾獎100週年,發行了六張紀念郵票。找了六位英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分別在宣傳的小冊子寫一些介紹的文字。Josephson在他寫有關量子力學的短文中,結論說有朝一日量子力學能幫忙解釋傳心術,引起英國科學界很大的反彈。牛津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David Deutsch直言Josephson胡說八道。他進一步說:「傳心術存在的證據實在駭人聽聞,假如工程師與醫生所接受的證明層次,跟支持特異功能的人落在同一水平上的話,全國的橋樑都要垮了,新的醫藥殺死的人會比治好的人還多。」
因為量子力學哲學性解釋的困難,以及量子論裡度量時觀察者的不可避免影響,使得很多人動不動就把一些特異現象推到講不清的量子現象。對於大腦認知功能裡是否真有量子作用的影響,也有像Roger Penrose所主張大腦微管的量子理論,雖然未經證實,但是通常被當作是一種有待實驗研判的科學假說。就像現在基礎物理裡最熱門的超弦理論,目前毫無作實驗證明的可能,但是物理學家仍然對它滿懷希望。然而像Josephson講的那一套卻得不到普遍的信任,如果要做一個對照,可看199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G. ’t Hooft的個人網頁(http://www.phys.uu.nl/~thooft/),他說大腦絕對不會對那些超乎尋常的量子現象敏感,所有特異經驗的解釋必然要來自心理學而非物理學。
如果科學家特異功能的興趣,純粹是對事物的存在與否好奇,影響的範圍恐怕比較有限。但是從前面提過的CIA研究就可看出,這裡面還潛藏了不單純的野心。類似的研究,在冷戰期的蘇聯也不曾忽視。至於在中國則有更為複雜的社會背景。八0年代在中國大陸把嚴新、張寶勝等所謂的大師吹捧上天。國家的資源被用來支持他們的活動,他們在北京出入有拉警笛的警車開道,國防科委封這些人營長團長。他們為什麼能這麼囂張呢?因為他們背後有國家首席科學家錢學森,有軍頭張震寰將軍等等顯赫人物撐腰。
錢學森在大躍進年代,睜眼說瞎話認為田產有可能增加20倍,結果捧昏了毛澤東對科學一竅不通的頭腦,革命的浪漫情懷造成了餓殍贏野的慘劇。因為錢學森是一位有出賣integrity前科的科學家,於是就有一種說法,認為正是因為中共的最高領導想用氣功、特異功能維持健康與生命,所以錢學森再次做出逢迎權貴的特殊貢獻。
如果我們去閱讀錢學森談論所謂人體科學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他確實是一位閱讀廣泛的學者,對於當代各類科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他也強調要區別封建迷信與真正的科學實驗,他也知道超心理學在西方的低落評價與地位。可是他仍然大言不慚說特異功能可能導致21世紀的新科學革命,也許比相對論及量子力學更大的革命。在他的推波助瀾之下,中國湧現了許多難以置信的奇人奇事。不少特異功能得到科學界的支持,這當中到底多少是趨炎附勢,多少是真心信服,在中國大陸那中威權社會裡,外人實在難以判斷。
不過中國大陸後來以于光遠、何祚庥、張洪林、司馬南等著名學者或新聞記者帶頭,對偽科學提出了反擊,揭穿了嚴新、張寶勝之流的作偽行為。其實大陸這一波反偽科學的活動暫時居於上風,並不見得就是對科學的深層性質有了堅定的認識。有相當的程度是因為法輪功的勢力對共產黨產生威脅,所以中共才大力推動科學普及以及駁斥偽科學的工作。于光遠等人訴諸政治力以對抗異己的方式,即使壓制了對手的反抗,其實對於擁護科學的自由思辯精神而言,並不足為訓。
在台灣研究特異功能的人,常常愛舉大陸有多少人體科學的研究機構,出版多少研究成果,或者他們親眼看了多少實驗。以大陸學界環境之複雜,以及不良學風之襲染,再加上在台灣不容易獲得充分的訊息與資料,往往只能姑妄言之妄聽之,難下什麼定論。尤其當以前那麼多功能人被揭穿過,也就不見得有必要一一檢查後續那些荒誕的宣稱了。因此在台灣要以這些大陸的事蹟作佐證時,必須特別謹慎,而且對於已經有反面證據的情形,更不應該完全避而不談。
對照於中國大陸的特異功能研究背後有政治力的介入,台灣的特異功能也不是純粹科學家自發的好奇行為。1987年在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的主動召集下,開始了台灣科學界的氣功與特異功能研究。當時參與的人也覺得在社會的大環境下,這些題材仍然屬於「怪力亂神」的領域,由國科會來主導「迷信」是一件不太妥當的事情,因此想了一個新名字「生物能場」來取代「氣功」。某些參與的人後來還洋洋得意,以為新名字達成減低阻力的效果。其實一個沒有操作意義的名詞,一個由科技官僚指定,迴避科學社群正常評審過程的研究計畫,嚴格講來根本是一樁違背學術倫理的蒙蔽行為。這跟國安局打著國家安全旗幟,動用秘密帳戶經費來逃避監督,本質上又有多大的差別呢?
在一個高唱要推動知識社會的台灣,從事正派科學研究的人,並不容易得到適當的鼓勵,反而經常要虛耗精力應付官僚體系裡各種無知與無聊的考核。但是搞特異功能這類科學邊緣活動的當權派,卻常常被社會瞎捧成「大師」,還得到科技官僚的主動關愛。這不也正反映了台灣社會對科學認知的膚淺,以及老想走捷徑的暴發戶心理嗎?不過前面說過,科學裡不應有禁區,要研究這些邊緣現象也沒關係,但是總應該有一些格調。下面來看看幾個基本的態度。
第一、科學之為科學,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內在自我批判與矯正的機制。科學裡沒有永遠的權威與絕對的真理。因此雖然有人以體制、結構、信念等等因素,把科學比擬為另一種宗教,甚至把堅持基本科學規範的人說成是「科學迷信」,但是在訴諸證據而非訴諸權威的分水嶺上,科學與宗教是早已分道揚鑣了。所以科學的研究活動與成果,必須放置在科學社群的公開場所接受批評。如果批評者理由不充分,自然不構成威脅。如果批評者找出破綻或證據不足之處,除了澄清論辯之外,就是繼續加強證據,或者承認確實有誤。
證據並不純粹侷限於實驗結果,實驗也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2] 科學是靠理論與實驗兩隻腳走路,沒有理論導引的實驗是盲目的。而理論不能是空想,它必須跟科學當時整個理論基架取得一定的協調。這並不排除理論革命的可能,但是革命豈會輕易取勝?一定要提出堅實的論證,並且說明以新代舊所得到的進步,才能說服別人接受新的理論。
在這種觀點之下,本土的「大師」動輒斥責別人沒作實驗,沒資格批評他們從事的特異功能研究,是完全違反科學精神的態度。前面提過對CIA委託研究的總檢討,確實需要專家深入研判,但結果還難取得共識。台灣的這類研究其實還沒到達那種程度,也就是說還不要在實驗細節與數據上檢討,便已經有很多令人質疑的作為。
再換一個角度來做對比,有所謂「白癡天才」症候(savant syndrome),一個一般智能很差的人,可能在某些特殊技能,譬如計算數字或繪畫上,有驚人的表現。我們並不會說這種大腦有缺陷的人具有特異功能。就算在世界上這麼眾多的人裡,有極端少數的人有異乎尋常的感官,譬如說手指真能認字,正當科學研究的態度是積極尋求自然的解釋,瞭解當事人的神經構造,而不是當作神通現象來對待。
第二、科學研究是要耗費資源的,如果資源的來源是屬於公共的領域,補助什麼研究就必須經過合宜的評審過程。對於具高度爭議性的題材,還應該有較公開討論,甚至辯論的程序。
台灣現在經濟狀況令人不樂觀,在科技上的投資,當然希望是有效率而能獲得有用成果。不論是提升理論的水準,還是達到致用的實效,都應該慎重選擇研究的主題。對於邊緣地帶的科學活動,最好由主其事的科學家向民間去募集資源。尤其當「大師」們把研究跟「靈」扯上關係時,不愁民間沒有熱中此道的金主。
在華人的天下裡研究特異功能,還有一項西洋人沒有的「利器」,就是「氣功」。氣功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已經變成一個複雜現象,它不僅僅是身體裡的變化,其實已經包容了社會、價值、歷史的多重內涵。現在台灣有一些人文學者著手全面研究這個現象,這是值得肯定的正當學術活動。但是人文學者可能誤以為這種研究裡應該有一個自然科學的層面,因此把特異功能與氣功的研究夾帶了進來。其實人文學者的資源應該用來探討,特異功能跟氣功拉到一處的社會因素,例如特異功能研究背後的情報作用,或者與當權者長壽夢的關連,這一類知識與權力的辯證關係。
第三、科學家對社會應該有相當的責任感。雖然要科學家移風易俗恐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在一個民間廣泛流行迷信的環境裡,科學家至少應該保持理性存疑的冷靜態度,而不要做一些譁眾取寵的媚俗行為。
當「大師」說去台大醫院捉鬼,又把武俠小說裡的藝術想像當作證據或者研究方向指引,把歷史上記載的裝神弄鬼傳說當作真實,又把所謂的「靈界」美其名為「信息場」,不少社會上的人就會說,科學權威都證實了靈界的真實,你們這些還在懷疑的科學家豈不都是心胸狹小的傢伙嗎?「大師」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不過以上提到的這些作為與見解,完全脫離現在科學社群能接受的範圍,「大師」不應該繼續打著科學的旗幟混淆視聽。「實事求是」應該是科學家對社會最基本的責任,要求科學家做到這一點,絕對不能算是過份的苛求。
總結上面所講的,對科學不友善的觀點或活動,有很深的歷史、社會與思想的來源,恐怕永遠也不可能完全絕跡。科學不斷面對這些挑戰,會促進自我的檢討與改進,也不見得就毫無正面作用。至於那些從事另類研究的科學家,他們通常會反唇相譏:「誰說我是反科學?」他們甚至會認為批評他們的人才是「反科學」,因為他們宣稱要科學更開明,容納更廣泛的議題。這些人的說法讓我們再次想到Holton所講的:「是一種精裝的、有機能的、有潛在威力的另類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包容了一種與通常科學迥異的『科學』。這種世界觀的歷史功能就是要在最廣泛的意義下,讓(一般的)科學喪失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的正當性。」但是自古很多推測式的假說都已經煙消雲散,燃素說到哪裡去了?永動機到哪裡去了?我們承認科學領域的邊界也許很難精確劃定,但是最終的裁判要靠證據、靠邏輯來說話,而不是靠貼「反科學」的標籤取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