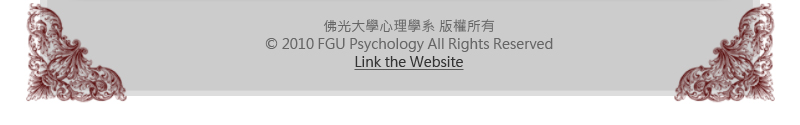捷思與偏誤取向研究
由Amos Tversky與Daniel Kahneman首開風氣之先的捷思與偏誤取向研究,想探討的是一般人在判斷與決策上的思考方式。根據捷思的觀點,我們的日常推理活動不可能像統計學家那樣,進行嚴謹而耗費心力的計算,而是使用一些簡便而通常有效的捷思法(見本章內文的說明)。然而,在正常的情況下,捷思法與嚴謹的計算方法所得的結果,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否則捷思法不會這麼有用)。在這個情況下,研究者事實上無法區辨推理的人實際使用的方法是什麼。
為了確定推理的人所使用的方法,研究者必須設計一些特別的推理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使用捷思法與正統的計算方法,會得出不一樣的結果,因此,研究者便可以根據受試者最後的判斷或決策與哪一種方法的結果相符,而得知受試者使用的方法。以Tversky與Kahneman(1973)的研究為例。實驗者播放兩段錄音給受試者聽,第一段錄音錄的是19個有名的男士(如總統尼克森)與20個比較不那麼有名的女士(如影星娜拉透納)的名字;第二段錄音則錄有19個有名的女士(如影星伊麗沙白泰勒)與20位較不出名的男士(如國會議員威廉傅爾布萊特)的名字。受試者的工作是,在聽完錄音後,判斷錄音中的人名男士較多,還是女士較多?
假如受試者的判斷依據的是人數的計算,則他們會說,在第一段的錄音中女士多於男士,第二段的錄音則反是。然而,實驗結果確是,80%的受試者認為,在第一段錄音中,男士多於女士;而在第二段錄音中,女士多於男士——恰與實際的計算結果相反。其後,對受試者所做的記憶測驗顯示,平均來說,受試者在聽過錄音後,對其中名人名字的記憶,比之於對較無名氣者的記憶,高出50%。因此,事情似乎很明白:受試者是根據記憶多寡對兩性的人數作判斷的。這正是可得性捷思法的做法。證據顯然支持捷思法的觀點。
在前述的實驗中,所謂「嚴謹的計算方法」當然是十分直接了當的。然而,當研究的方向指向代表性捷思時,情況就要複雜多了。譬如說,在Tversky與Kahneman(1983)的一個實驗中,實驗者給受試者看如下的故事:
「琳達31歲、單身,直率而聰明。她主修哲學。當年在學校唸書的時候,非常關心歧視問題與社會正義,也參加反核遊行。」
在讀完這段簡短的描述後,受試者被問及,琳達可能是怎樣的人:小學教師、書店員工且加入瑜珈班等等,共有八個選項。其中有三項是實驗者感興趣的:活躍的女性主義者(F)、銀行行員(T)、銀行行員兼活躍的女性主義者(T&F)。受試者必須估計的這八個選項是正確答案的機率,並據以將這八個選項依其可能性的大小排序。根據機率原理,琳達如果是個銀行行員兼活躍的女性主義者,則她必是個銀行行員。換句話說,琳達是「銀行行員」的可能性不會小於她是「銀行行員兼活躍的女性主義者」的可能性。用機率符號來表示,即P(T)³P(T&F)。因此,如果受試者式的思考方式符合機率原理,他們就會將「銀行行員」的可能性排序,排得比「銀行行員兼女性主義者」高。然而,實驗結果顯示,不論受試者有沒有修過基礎統計學(裡面含有機率的概念),乃至於修過進階課程,有85-90%的人,在排序上違反了上述的機率法則。換句話說,受試者顯然並未以合於機率法則的方式思考。
顯然,由於琳達的個性看起來很像典型的女性主義者——喜歡談哲學、對關心公平正義、勇於表達等等,因此她當然比較像「在銀行工作的女性主義者」,比較不像小心謹慎、按規矩辦事的「典型銀行行員」。準此而論,假如受試者根據「琳達看起來像哪類人」去做反應,他自然會覺得,琳達是「銀行行員兼女性主義者」的可能性高於她是「銀行行員」的可能性。這正是運用代表性捷思法的具體表現。因此,這個實驗結果又再度支持了捷思法的觀點。
這種捷思與偏誤取向的研究,自1970年代發端以來,研究成果蔚為大觀,引起廣泛的注意,對於我們了解人類的推理方式,有很大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