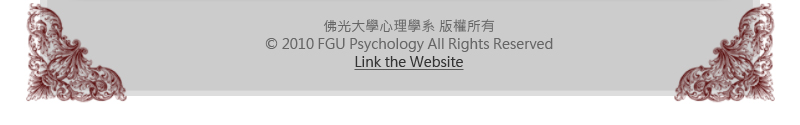概念與語言
在語言中,我們用語詞來代表概念。語詞是由一組語音(稱為音素,phoneme)組成的。只要拿幾種不同的語言來略做比較,就會發現,各地的人常用極為不同的一組語音指涉同一事物。譬如說,英語中的book與漢語中的「書本」(包括台語中的「書」、「冊」),即是以截然不同的一組語音來指涉同一事物。因此,語詞與其意義之間的關係是「約定俗成」的。基本上,語詞的意義決定於他所代表的概念,而概念則決定了語詞的指涉範圍(extension)。例如,「書本」這個詞代表「由印有文字或圖畫的紙張裝訂而成的冊子」,而這個定義則決定了哪些東西可以稱為「書本」。因此,概念是介於語詞與其指涉的事物之間的中介者。
然而,這樣的想法卻受到哲學家Hilary Putnam(1975a,1975b)的挑戰。Putnam指出,我們有可能使用某個語詞,卻對它背後的概念一無所知。譬如說,我們常常聽到與使用「基因」這個字眼,然而,多數人對它的真正意義卻「毫無概念」。事實上,日常用語中充充斥著各種專業字眼,常常是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但是卻無礙於我們使用這些語詞。當我們使用這些字眼的時候,我們只是用它來指涉某個事物——譬如說,指涉某種與遺傳有關的物質。即使我們並不了解它的意義(不知道他的界定特徵,腦中也不存有它的原型),也無礙於我們的指涉。
這樣一種語詞的使用方式發生在Putnam所謂的自然類用語(natural kind terms)上。這類用語是用來標示「自然發生的事物」之語詞。相對來說,諸如「單身漢」、「三角形」這類用語,標示的是依人為標準歸類的事物,則稱為名目類用語(nominal kind terms)。顯然,自然類用語指涉的事物正是科學家或其他專家研究的對象,而這些專家研究的目的之一則在於釐清這些事物的性質。根據這樣的想法,Putnam主張,我們使用自然類用語時,有一種「語言上的分工」(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存在,我們使用這些語詞來指涉某些東西,至於那是什麼東西,則取決於專家的說法。譬如我們常用「水」這個字眼來指稱某種液體,至於水是怎樣的液體,它的化學成分與物理性質為何,說話的人未必清楚。在這個情況下,說話者對於水的概念,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信念:它是一種有某些專家了解的物質。
Putnam的想法顯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從語言的一面來看,他指出語詞有不同的類別,因之有不同的用法,有些語詞並不對應到描述性的概念,在此情況下,概念並不賦予語詞意義,它的唯一功能是指涉某些事物。從概念的一面來看,Putnam的觀點直接挑戰了傳統關於概念是一堆描述性資訊的觀點。我們都曾從專家的研究結果獲取某些較為成熟的概念,譬如關於「水」、「基因」等的概念,在這個情況下,所謂概念,其實是個理論。準此而論,我們腦中許多關於自然類事物的概念,可能都像理論,內容是關於概念的個例會有哪些特徵、哪些事物可以包含於概念類別中、概念與概念的關係為何等等的一些解釋性說法。這樣的概念當然是會改變的,或者根本是錯的。
Putnam的想法雖然是從哲學分析出發的,這樣的想法卻促發了心理學的許多新觀點與新研究(例如,Lakoff, 1987a, 1987b;Medin, 1989;Medin, Wattenmaker, & Hampson, 1987;Rips, 1989)。 |